文 / 郭葳

《Adiemus:Songs of Sanctuary》(“圣域之歌”、“颂歌之歌”)是不可思议的作品。在店里我把它看成了“Amadeus”(莫扎特),到家越听越不对,这哪儿是莫扎特!分明是卡娜娃与毛利歌手合作的太平洋岛歌。“Adiemus”不是“Amadeus”,跟莫扎特没关系。威尔士作曲家卡尔·詹金斯创作了这奇特的歌曲,1994年以单曲发行,日后成为他系列创作的总标题。
“Adiemus”非现存语言系统中的词汇,无法准确翻译,《圣域之歌》是第一部专辑,1995年发行,九首歌曲。“圣域”表明了歌曲的圣咏性质。专辑开篇是《Adiemus》,其余八首为《钟声》《不成比例之歌》《非同寻常之歌》《回到天堂》《重复之歌》《爱》《香山》和《赞美诗》。再次强调,《圣域之歌》的所有歌曲,从标题到歌词不属于任何既有的语言系统,90%以上的词汇没有确凿的来源,只能连蒙带唬。单就“Adiemus”来说,比较接近的是拉丁词“adeamus”,意为“让我们接近”(或“让我们向仲裁者提供一个理由”);再就是拉丁语动词“audire”(听)的两种形式:“audiemus”(我们将听到)和“audiamus”(让我们听到)。专辑的第五首《重复之歌》(Cantus iteratus)差不多是意大利语;第六首《Amate adea》(爱),“Amate”为“爱美”或“爱情的”(amare)复数形式;“adea”是音节,无任何词义。这些高贵的渊源增加了Adiemus的神秘,但正如作者本人说的,创作时他没想那么多。

圣域之歌“Adiemus”系列歌曲的主要结构是古典的(改良的回旋曲),“音乐语言”是古典与“世界音乐”的混合,和声兼有福音歌曲与非洲音乐的特征,打击乐是半个灵魂,让歌曲的圣歌气氛流露出乐观的部落风格。詹金斯在创作过程中尽量避免使用2/4、3/4、4/4等传统“笔法”,最大胆的是毅然去掉了传统“语义”对“歌曲”的支持,让“新词汇”在没有词义限制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推动音乐。“Adiemus”的音节很少以辅音结尾,这一点与日语、毛利语和非洲语言相似,性质却截然不同:它们不是词汇,是人所能捕捉到的最佳状态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Adiemus”是一流的音乐文字,发明者是一流的语言家。
听“Adiemus”是个必遭愚弄的过程:乐队、人声合和自然、清晰流畅,非常好听;歌者所唱,初以为某个外语,三番五次后便要确定到底是哪门外语,狠狠耍了一圈,回头发现,他们有滋有味唱的“外语”是一堆“呼儿嗨哟”的“假话”:词是“假”的,字是攒的;语言似有内容,实际毫无意义。这是人为的“音节语”,发明者的核心概念是“允许将自由的声音作为音乐创作的工具”,就是把声音当“仪器”用。这应该不是詹金斯独有,类似的概念90年代中后期的“新时代音乐”和“世界音乐”中已然流行,如1992年范吉利斯(Vangelis)为电影《1492:征服天堂》创作的音乐,法国作曲家艾提安·派胡尚(Étienne Perruchon)的交响乐套曲《多古拉之歌》(Dogora Ouvrons les yeux)等等。我觉得詹金斯“音节语”的胜利不是诸如此类的概念的胜利,而是概念最终实现的胜利。詹金斯的创作意图亦并非通过简单摆弄音素来制造一种音乐的附丽,如一些作者在布道歌或交响乐上的处理,无论如何附丽是从属的、无主权的、不独立的,它在一部作品中的价值和意义,取决于该音乐对传统语言的一般要求,同“音节语”独立自主的品质不可并论。

归根结底这是疯狂的尝试。詹金斯之前,恐怕没有人以这种方式使用单词,别说“假词”了。有听众花几个月的时间,试图找出adiemus实际使用的语言,最后惊讶地发现,那是一种完全不认识的单音节语言……作者是天才!我认为詹金斯不仅天才,还是疯子,“造假”只是第一步。为避免“呼儿嗨哟”分散听众的注意力,这疯子还把那无中生有的东西风格化了。歌曲成了魔圈:没有可理解的词汇,但听起来很美;听众每听一次似乎都增加了对“假话”的理解,终却一无所获。下面是adiemus合唱部分的“文字”:
A-ne-ma-ne-coo-le-ra-we, a-ne-ma-ne-coo-le-ra,
A-ne-ma-ne-coo-le-ra-we-a-ka-la
A-ne-ma-ne-coo-le-a-we-a-ka-la (a-ya-do-wa-ye-)
A-ne-ma-ne-coo-le-ra-we-a-ka-la (a-ya-do-wa-ye-)
A-ya-do-wa-ye
A-ya-do-wa-ye-e-
不知所云。这些词不具“词”义,是排列的“乐器的声音”。它们听起来很像语言,也具有所有“语言的声音”,但不同于传统。从语言与音乐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来看,它们是依乐而立,像缝在音乐上似的。几年前我看过一篇论文,内容针对语言重音与音乐节拍之间的关系。作者的结论是:如果将歌曲中的语言重音与音乐节拍做对应的调整,不仅可以加强听众捕捉节拍的机会,同时会增加聆听者对词义的理解。此结论支持了一个有争议观点,即认为在一部歌曲当中,文字与音乐节奏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关系。音乐处理与语音调整之间确实存在差异,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二者在性质上有强烈的重叠。
从过去到现在,作曲实践中常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词曲关系,这方面“Adiemus”是成功的,其“音节语”的特点也令我想到汉语(也是单音节文字系统)。对汉字歌曲,中国传统上有“字可顺曲,曲不能顺字”的认识。写歌作曲……词强曲弱、词弱曲强都不是好的追求。而单音节文字的困难在于:“词顺曲”,没准儿不顺意;“词顺意”可能不顺耳。为求意、节、韵的三合,解决之道是引入无实际意义的语助词,达到所谓“一唱三叹”的效果。传统民歌有很多杰出的例子,最典型的莫过于晋西北民歌《芝麻油》里的“呼儿嗨哟”——“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
翻译家金伟曾谈到:“日本古代歌谣里有不少叠语,日文里有一个专门称呼,口字旁加一个杂字。就是无实际意义的语助词,有点类似汉语中的‘呼儿嗨哟’”。“Adiemus”跟日语有些近似,算是日语的“呼儿嗨哟”吧。好了,读懂“Adiemus”的不可知论不难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它的全部词汇认成语助词,听成“呼儿嗨哟”。而且……它真没有意义吗?
“Adiemus”没有“真正的单词”,对这些“呼儿嗨哟”的歌曲,有人无感;有人联系到情绪;有人山川湖海、奔腾宁静;有人引申到婴儿诞生、沙漠日落……还有:“我每次听到它都会哭泣,它让我想到地球,多美我们都认为理所当然,如果早点儿开始关注它,我们会得到多少回报。这歌绝对是惊人的。曲调如此舒缓,竟没有描绘任何具体的东西,只有纯粹的音乐”。“它也许没有合理的歌词,但它包含的内容是一种品质,可以让内心的悲伤倾泻而出”。怎么说呢,有点儿感动不是吗?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Adiemus有真正的单词,语助词有实际的意义。

“呼儿嗨哟”比犯傻强听“呼儿嗨哟”的感觉是“不懂,但非常好听”,听外语歌曲,尤其歌剧咏叹调之类,也是“不懂,但非常好听”。记得当年向朋友推荐贝利尼的歌剧《诺尔玛》的“圣洁的女神”(Casta diva),过程中他的表情随着旋律的变化而变化,最后说了句“太好听了”!是,我们不懂意大利语,但肯定听懂了,因为陌生的语言变成了纯粹的声音,声音是普遍的,就像空气和水,不可能不懂。理论上说,音乐与逻辑语言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一系列“正确”或“错误”的声音。声音是普遍的,表情、内容、意义则起于个别的内心,随着“不明词义”的宣叙、咏叹,化作墙上的斑点或窗外的树影婆娑,所谓意境就是心境,语言乃心语,可随时转化为文字。“不懂意大利语,所以意大利歌非常好听” ,起码在谈论歌剧的时候,这话未必不能说。
歌剧演出使用“民族语言”、“地方语言”还是原创语言一直有争议。威尔第的《唐·卡洛斯》在巴黎首演时用法语,意大利的首演作了修改。瓦格纳的歌剧在意大利演出,很长时间都是用意大利语;雅纳切克的歌剧在英语国家演出时选择了英语。假如作曲家真的期待自己的作品在异国他乡时使用异国他乡的语言,世界上所有的歌剧院坚持以地方语言演绎歌剧是百分百合乎逻辑的,然而……没有一家歌剧院坚持这么做。到底是嫌麻烦还是没必要?

逻辑是普遍的。我们必须相信,在处理音乐、语言和噪音方面,音乐家比常人更具感知的优势,他们有足够的直觉和技能,在他们最熟悉的语言上处理音乐。这方面,马里兰大学和西北大学的专家斯瑞德和克劳斯可以提供神经学或神经心理学的实验证据。不过……还是算了。犯傻也有神经学的论据,可我真没法儿把犯傻视为天赋。语言和音乐的问题……还是老调重弹吧,语言的某些词或句子有意义,有些没有;音乐也如此,一组音符听起来很好,另一组却不咋地。还有就是解释的问题。词义的解释意味着普遍的理解,即一个词或句子,对很多人来说具有相同的意思;音乐的解释很难达到那种普遍性,同一首乐曲,每人的解释不尽相同。二者的差别或许意味着歌词对音乐是一种的限制,差劲儿的歌词是毒药,更别说差的翻译了,那是火灾。
回到开头的问题:歌剧演出要用“民族语言”、“地方语言”还是原创语言。先看雅纳切克,美妙的捷克作曲家,其音乐语言完全基于捷克语的语音节奏,当他的歌剧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时候,一些主要动机就成了废话,因为雅纳切克的笔记与捷克方言的词语变化有关,这些变化在翻译过程中没可能完整地表达出来。再看《托斯卡》。不妨引述澳大利亚一位学者的话:“……就我个人而言,毫无疑问,无论翻译多么有趣,在语言与‘普契尼音乐’的结合上,意大利语比英语更能制造令人满意的体验……当卡瓦拉多西在《托斯卡》第二幕唱出惊心动魄的‘维多利亚!维多利亚!’的时候,意大利语的元音与音乐完美连接!英语的‘胜利!胜利!’根本无法表达相同的情感,普契尼的音乐也会因此而达不到同样的戏剧强度,无法产生作曲家期望的那股力量”。最后……看我的。我知道《茶花女》《卡门》有中文版本,演唱用的是普通话。能不能来个广东话?河南话?《卡门》到印度该怎么办呢?世上有多少人想听印度(印地)语的《阿伊达》或缅甸语的《女人心》呢?答案是:听一遍“Adiemus”再说 。不论“胡言乱语特别好听”还是“不懂,但非常好听”,“呼儿嗨哟”总比犯傻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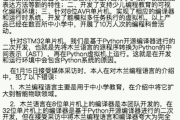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