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移民史与重庆方言

一个地方的语言与该地人民息息相关,人口的大量迁入迁出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对语言产生影响。
重庆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历史上有多次大的移民活动,使本土的居民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也使重庆的语言发生了很大变化。
例如,历史上多次从湖广移民、黔、渝等地,把不同时期的湖广话带入重庆。今天的重庆方言正是重庆土著方言与湖广方言相结合的产物。
重庆一些方言岛例如荣昌的客家话和老湘语、潼南龙形镇的老湖广话、梁平龙门镇的土门场话等都是各个时期移民原语言的遗留。
(一)重庆历史上的移民活动
1.早期的移民

重庆人自称是巴人的后代,但是巴族的起源并不在重庆。巴人原活动于今湖北省南部、西部和汉水流域一带。
展开全文
巴人受当地楚人逼迫,多次发生巴楚战争,巴人处于劣势,逐渐后退,被迫迁入重庆地区。巴人由东而西,这就是最早的移民。
现重庆所辖广大地区,在古代是蛮荒之地,居住着“濮、苴、共、窍、奴、谯、夷、蜑”等民族,这些民族在中原诸夏眼中是“蛮夷”、“西南夷”。
巴人进入重庆地区后,与当地土著居民杂居共处,建立了以部落联盟为基础的奴隶制国家,以江州为中心,达三百多年之久。
外来的巴人与重庆当地的土著居民都是在巴国的统治下,故也统称为巴人或巴族。在一个比较封闭的地区内,各族人民相互交流,相互学习,互相影响,逐渐形成一个有统一语言、统一文化的共同体。

武王灭纣后,把自己的宗亲分封到巴国,这一举措加强了巴国与中原地区人民的往来,在语言、文化上都会有一定的交融。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立36郡,巴郡就是其中之一。为了加强统治,秦始皇迁“秦氏万家”入巴蜀。这样,中原地带人口的大量迁入,加上政治和文化的影响,使原来的土著居民包括巴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逐渐在语言和文化上与中原地区趋同。《文选》四载左思《蜀都赋》刘逵注引《地理志》说,秦灭巴蜀之后,“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
以后,地处西南隅的历代重庆地区人民作为中华大家庭的一员,生活习俗、语言等方面与其他地区的汉人逐渐融为一体。
2·元未明初的大规模移民

元末明初时战争频仍,为了躲避战乱,人们往往扶老携幼,举家外逃,而地处西南隅、偏僻荒芜的重庆广大地区往往是中原地区尤其是相邻的两湖地区人们的首选。
元朝末年,湖北罗田人徐寿辉率领的红巾军在长江中上游起义,其部下湖北随县人明玉珍于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年)率军由巫峡入川,陆续占有川蜀之地。至正二十年(1360年),徐寿辉部下陈友凉弑杀徐寿辉自立为汉王。
明玉珍拒不受命,自立为陇蜀王。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明玉珍称帝,国号夏,定都重庆。1366年明玉珍死,子明升继位。1371年朱元璋派兵入蜀,明升降。
明玉珍及其子在重庆15年,其部下多为湖北人,大夏政权灭亡后,其数万部下多留居重庆。在明升投降之前,明朝官军占领湖广后,原住湖广地区的与红巾军有奉连的人为防备明朝官兵捕杀,也纷纷迁入重庆地区。
如石柱的《谭氏家谱》记载:“在元未徐寿辉、陈友凉互争雄长,天下大乱时,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初二日辰时,父兄子侄七人,从湖北麻城孝感珍珠码头起身入川。”
垫江县永安乡梅氏族谱记载,其始祖梅玉润于明洪武二年,从河南迁来定居。
明朝建立后,为了社会稳定、发展生产,中央及当地宫吏大规模组织移民,鼓励其他地方的百姓尤其是湖广百姓大量迁移入巴蜀。如石柱的《向氏家谱》记载:“大明平定西川,逐陈填楚,逐楚填蜀,洪武二年始祖向玉、向瑨二人由麻城入蜀,落业密酿坝猫槽沟(今悦来乡)。”
《黔江旧志类编》载陶姓家谱:“明洪武时由江西抚州金溪县迁四川川大足县,嘉靖时迁本邑。散居全溪、白合、黑溪,共千余家。”
元未明初由湖广迁入的人以麻城人最多,除了避难的外地“流民”之外,外来移民也有战争中落业重庆各地的官兵。
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派大批明军分别从北面和东面两路攻打明升,重庆平定之后,大批外地军人留居重庆。如《石柱县志》所引《刘氏族谱》记:“洪武四年,马克用不能就敌,求友德率八骑等处兵将七千七百,鏖战十有九日亦不能胜,于是尽拿家口,搬移四川地方溪源里置业落坐,此后子孙分支落业石往等地。”
另外,重庆地区历史上有多种少数民族,由于民族歧视政策,宋、元、明等朝代都有“平蛮”、“赶苗”的情况,在战争平定之后,一些官兵就落户重庆地区,以后子孙也在此世世代代繁衍。如《石柱县志》所引《马氏族谱》载:“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马定虎平五溪蛮,授石硅安抚使,.…,后代子孙散居县内各地。”
《石柱县志》引《向氏族谱》载:“明末向时梅、向时桂兄弟,随秦良玉讨奢崇明、御罗汝才有功,辞官解甲,分别落业溪源里七甲官渡河和野鹤溪(今桥头乡),繁衍生息。”
《彭水县志》引湖北咸丰活龙坪《秦氏家谱》说,元季时,(秦)思安“官千户邑,生四子,从湖北汉阳府孝感县携四子赶苗到四川省彭水县长潭(滩)坝落业”。
3.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

明未张献忠起义,社会动乱,百姓民不聊生,既逢连年战乱,也遭遇严重的自然灾害。地处战乱中心的湘鄂赣等地的很多百姓举家往重庆的各偏远地区迁移。
《忠州直隶州志》载:“崇祯十七年,张献忠由夔门上,…人多避乱石硅。”
《石柱县志》引《李氏族谱》载:“明末避乱,由湖广元州芷江县辗转迁石硅洞源里四甲马武坝落业。”
而四川人口经过战争动乱和灾荒,也急剧减少,全川人口仅存50万左右,大量人口为躲避战祸而迁徙流亡,更多的人则死于饥饿、疫病和战乱。清嘉庆时所修《四川通志》谈到当时情况时说:“合全蜀千里内之人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因为张献忠大兵曾经经过重庆,所以重庆所受破坏更为严重。
咸丰时期修订的《开县志》云:“国朝顺治初,张献忠复入蜀,屠杀无算,靡有子遗,开县人民所存仅止数姓而已。”
除了兵灾以外,清末的数次天灾也是加剧人们苦难的重要原因。
清顺治三年(1646年),重庆大旱大疫,"几无遗民”。顺治五年(1648年),重庆又大旱,"斗米三十金,无售者”。江津县“十年左右人烟断绝”,“群虎白日出游”。
清康熙元年(1662年)四川总督驻节重庆,当时重庆城“为督臣驻节之地,哀鸿稍集,然不过数百家”。其他县城更是人烟稀少。如原本人口繁荣的合川州城(今合川县城)康熙六年(1667年)统计仅剩140余人。
以后,随着清政府统治的逐步巩固,社会相对安定,本地外流人口纷纷返回定居。
另外,清政府为了恢复四川经济,迁移湖广、江西、陕西、福建、广东等省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进入四川(包括重庆)。
为了吸引百姓迁入,清政府采取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措施。
康熙七年(1668年),清政府批准招抚四川外逃的流民回原籍开垦;康熙十年(1671年)批准四川向邻省招民耕种,规定抛荒土地开垦后可永占为业,准令“五年起科”(即五年后才开始征收赋税),并以招募民众数量作为官吏晋升条件:“现任文武百官,招徕流民三百名以上,安插得所,垦荒成熟者,不论俸满即升;其各省候选者州同、州判、县丞及举贡、监生有力招民者,授以署县职衔;系开垦起科,实授本县知县。”(《清朝文献通考》卷二)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又改为“诏民间垦荒田亩,以十年起科”。从此,江西、湖北等省的民众便大量迁入。据乾隆《垫江县志》记载:“原住人户流亡殆尽,招移填住多自外来,而楚籍尤众。”
民国《巴县志》卷十载:重庆“自晚明献乱,而土著一空,外来者十九皆湖广人”。
这段移民史从很多人家的家谱中都可以看出来。石柱的《黄氏族谱》载:“于康熙年间奉诏填蜀,携带全家同四邻友好周、李、包等七姓一道,在石柱府洞源里四甲黄鹤坝一带落业。”这些百姓入川渝后,往往亲朋同乡相邻。
梁平县龙门镇汪家沟的汪氏家族现有数千人,《汪氏族谱》载其祖先“于康熙三十六年携子入川,置业于梁乐善乡西山沟”,“吾梁西山沟汪氏,康熙中年来自湖南永郡之零陵”。该家谱还叙述了当时部分移民在重庆和四川的大致分布:
“其自衡阳迁者,为巴县,为广安州,为安县,为合州,为渠县,为垫江,为岳池,为伏州。其自祁阳迁者,亦为巴县,为中江,为资州,为万县,为新宁。其自零陵迁者,为梁山,为开县。去数百里,合计近千丁。”
“其自衡阳迁者,为巴县,为广安州,为安县,为合州,为渠县,为垫江,为岳池,为伏州。其自祁阳迁者,亦为巴县,为中江,为资州,为万县,为新宁。其自零陵迁者,为梁山,为开县。去数百里,合计近千丁。”
这种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始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历经100年左右。全国各地有湖南、湖北、广东、福建、江西、云南、贵州、广西、陕西、山西、浙江、山东、安徽、江苏等14个省约623万人迁入巴蜀地区,其中以湖广省(当时行政区名,辖今湖南、湖北,雍正十七年即公元1812年才分为湖南、湖北两个省)人最多,约346万,占55.5%。
人们常说的“湖广填四川”就是指从元未以来一直到清代发生的多次大规模湖广等地百姓向川渝迁移的情况,主要是明末清初。
《魏源集湖广水利论》云:“当明之世,张贼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apos之谣。”
有些地方的人口结构和风俗反映出不同时期的移民情况,如咸丰四年(1854年)撰写的《云阳县志·风俗》云“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洪武时由湖北麻城孝感奉敕徙来者;北岸民则皆康熙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南、北人较多。而风俗则南岸俭而北岸奢,迥然不侔矣。”
4抗战时期的移民

抗日战争时期,半个中国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重庆作为国民党政府的“陪都”达八年之久,大量北方和东部沿海的人民涌入重庆,全国精英云集重庆。
据统计,抗战八年,大约有100万以上人员迁移到重庆市及其附近沿江地区,重庆市人口增长了1.23倍,外地迁渝人口占重庆市人口一半以上。这些抗战移民多是企业家、工商业者、军政官员、知识分子和工人,他们的到来直接带动了重庆城市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大量的外来人口,长期住在重庆,这对重庆的语言肯定会有很大的影响,语音、语法尤其是词汇都会吸收进一些外来成分。这也是重庆话与相邻的四川川地区有所差别的重要原因之一。
上述几次大移民,奠定了重庆方言的基础。
虽然以后还有一些移民活动,如20世纪50年代初多达58万多人的南下干部及其家属南迁;60年代的三线建设,大量沿海地区工厂内迁,随厂迁移过来大批工人、干部、科技人员等,但规模都不及前几次大,所以除了一些词汇的引入外,对语言系统的影响不大。
虽然以后还有一些移民活动,如20世纪50年代初多达58万多人的南下干部及其家属南迁;60年代的三线建设,大量沿海地区工厂内迁,随厂迁移过来大批工人、干部、科技人员等,但规模都不及前几次大,所以除了一些词汇的引入外,对语言系统的影响不大。
移民与方言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移民的大规模迁徙会引起语言的分化或融合,移民史可以用来解释方言的部分成因,反过来方言也可以为移民史提供有力的佐证。
中国历史上常把非华夏族的其他民族称为“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云:“巴郡南部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谭(音审)、相氏、郑氏。”可见古代巴人也是一种“蛮”。
语言是民族的重要标志之一,远古巴人既非华夏族,其语言也当不同于汉语。古代巴人建国后,从殷商时代开始,就与中原地区有了交往。
武王伐殷成功后,派其宗亲管理巴国,使巴地直接隶属于当时的中央政府,这些措施肯定在语言和文化上都会给巴族以重大影响,使之向中原民族趋同,逐渐汉化。
《文选·宋玉《对楚王问〉》记载道:“客有歌于郢中者,歌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之者数千人。“
可见巴人歌曲当时是楚国都城最流行的歌曲,如果时巴人说的不是汉语,不会使数千楚国人跟着唱,这也可看出春秋战国时巴人语言与当时楚人的语言具有相当大的一致性。
秦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打破了部族之间的樊篱,并大量向地广人稀的巴蜀地区迁移中原人,加强了民族之间的联系,使巴人与中原人生活于一个大家庭之中。
虽然早期巴人说的不是汉语,周代及周代以后,由于与中原地区人民的密切往来,杂居相处,再加上华夏语的强势地位,使巴人的语言演变成为以华夏语言为基础结合巴族语言的独具特点的语言。
《华阳国志·巴志》引了多首巴地先民的诗歌,其一是:“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喜谷旨酒,可以养母。”从用词和用韵来看,这些诗歌与中原地区的诗歌是一致的。
战国时代,东汉扬雄《方言》里有十多处记载了“梁、益”之间(即陕西汉中地区和巴蜀地区)的说法,并与秦、晋、齐、楚等地方言相提并论,可见,当时也是认为巴蜀地区的语言属于汉语大家庭中的一员。
早期的重庆方言已不可考,现代重庆方言的定形当是“湖广填四川”之后。
大量移民的迁入和五方杂处的人口结构,对重庆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使语言发生了很大变化。
清光绪年间编的《铜梁县志》(上)云:“土著者百之一,楚黔两省人最多,亦有自闽粤江右来者。”光绪版《塞州府志》云:“夔州部土著之民少,荆楚迁居之民多。”
1993年出版的《垫江县志》也称:“构成县人主体的是清朝从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等省迁来的移民。”
1993年出版的《潼南县志》统计了潼南37个姓氏家族,只有三个姓氏的家族为明末战乱前的本地人,其余34个姓氏都来自外省。这些移民活动对重庆地区的语言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来自不同地区的外来人口带来了不同的方言,这些方言与当地语言结合逐渐形成了当今的重庆方言。
在湖广填四川之初,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各个方言区的人杂居一处,语言比较混乱。
例如,清《城口厅志》载:“民少土著,五方杂处,乡俗不同,土音各别。”
民国《云阳县志》云:“云阳僻处蜀东,流贼之乱,居民流亡以尽。康乾以还,始由湖南、北人徙居之故,方音往往杂以楚语。不惟上溯《方言》多不相符,近如《俗言》、《蜀语》亦多违异矣!”
民国《云阳县志》云:“云阳僻处蜀东,流贼之乱,居民流亡以尽。康乾以还,始由湖南、北人徙居之故,方音往往杂以楚语。不惟上溯《方言》多不相符,近如《俗言》、《蜀语》亦多违异矣!”
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云:“明清间自楚赣来迁者十六七,其遗传不尽随山川而变也。五方语言之异以名词各随沿习,不能强同。故闽粤之人必学官话,其土音有同邑所不尽解者。…明多湖北籍,清增江西籍,奕世不忘其本,吐嘱非毫无意义,或音以轻重而差,或声以通转而讹。”
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云:“明清间自楚赣来迁者十六七,其遗传不尽随山川而变也。五方语言之异以名词各随沿习,不能强同。故闽粤之人必学官话,其土音有同邑所不尽解者。…明多湖北籍,清增江西籍,奕世不忘其本,吐嘱非毫无意义,或音以轻重而差,或声以通转而讹。”
清光绪年间编制的《永小川县志风俗方言》谈到当时永川的人口和方言状况:“土著复业仅十分之二三,至今土满人稠,强半客民寄寓。故部属城市均有各省会馆,唯两湖、两广、江西、福建为多。生聚殷繁,占籍越十余传而土音不改。一父也,有呼为爹、为爷、为伯伯、为阿爸者;二母也,有呼为娘、为妈、为母亲、为阿mi者;子,或谓之儿,谓之崽,谓之幺;兄,或谓之哥,谓之长;弟,或谓之小,谓之胎。见物美者,通称为好,而或日标、日艳、日都、日佳。见物盛者,通称为大而或日庞、日硕、日夥。指物所在,日阿堵、日这个。办事迅速,日忙溜,日快当。凡厥名物器数,言甚庞杂,不能殚述。”
清光绪年间编制的《永小川县志风俗方言》谈到当时永川的人口和方言状况:“土著复业仅十分之二三,至今土满人稠,强半客民寄寓。故部属城市均有各省会馆,唯两湖、两广、江西、福建为多。生聚殷繁,占籍越十余传而土音不改。一父也,有呼为爹、为爷、为伯伯、为阿爸者;二母也,有呼为娘、为妈、为母亲、为阿mi者;子,或谓之儿,谓之崽,谓之幺;兄,或谓之哥,谓之长;弟,或谓之小,谓之胎。见物美者,通称为好,而或日标、日艳、日都、日佳。见物盛者,通称为大而或日庞、日硕、日夥。指物所在,日阿堵、日这个。办事迅速,日忙溜,日快当。凡厥名物器数,言甚庞杂,不能殚述。”
可见在来源复杂的情况下,有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各种方言混杂,同时并存。不过,由于人们交际的需要,语言不通的情况不可能长期存在。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方言相互影响、融合,会逐渐形成一种为各方面所接受的通用方言。
民国重修《大足县志》记载:“本县语言旧极复杂。凡一般人率能兼操两种语音:平时家人聚谈或同籍人互话,日打乡谈,粤人操粤音,楚人操楚音,非其人不解其言也;与外人交接则用普通话,远近无殊。”
而这种“普通话”就是在各地纷繁的语言环境中形成的通用方言。
移民以前,重庆地区原住民有自己的方言,社会安定后,大量外逃的原住民迁回原籍。移民早期,方言混杂,各说其语,但移民毕竟处于客位,况且其方言来源庞杂,不易统一,因此处于主位的原住民的方言当时应该属于强势方言,只是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他方言的影响而产生变化。
由于移民以湖北人为多,而湖北话也属于北方方言中的西南官话,与重庆地区的原住民的方言大多相通,所以后来通用的方言应该是以原住民的方言为基础结合湖北话,并吸收了其他方言的一些成分的基础上形成的。
从形成区域的先后来看,当首先是在作为一个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中心城市即重庆主城形成,然后由近及远逐步扩散到各区县。而当一种方言占上风时,其他方言会逐渐受到其打压,缩小其使用范围,乃至完全消失。
清末和民国初年重庆地区的语言基本上就日渐统一。
民国修的《云阳县志》就说道:“蜀中语言,各县同者八九,异者一二。”
民国重修《大足县志》说得更具体:“近三四十年来,普设学校,适龄儿童,出就外传,乡谈遂失其传。惟中敖场之玉皇沟一带,其居民以原籍湖南之永州、会同两处者为多,领白之叟尚能乡音无改也。”
可见在当时,语言已趋统一,即使在同籍人聚居区也只有老年人能说其原籍音了。
现在,重庆一些地区有同一意思用不同词表示的情况,就应该是过去五方杂处时语言混乱现象的遗留。
例如大足话叫蜻蜓有“点灯儿”、“咪咪羊”、“丁丁猫儿”等多种叫法,称祖父有“爷爷”、“公”、“阿公”、“爹爹”、“大大(阴平)”等称呼,就是明显的例证。
像奉节县,语言根据海拔高度的不同和城镇与农村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海拔高的地区如竹园镇和兴隆镇的平舌音和翘舌音区分得很清楚,而海拔低的康乐镇、草堂镇和城关镇都说成平舌音。位于中间地带的朱衣镇和吐祥镇的情况位于二者之间。而同是兴隆镇,生活在镇上的人大多把翘舌音发成平舌音,并以此为荣,这是因为县城的人不分平翘,而生活在乡下的人则一律分平翘。这个事例也可以说明在语言演变过程中中心地区的语言对其他地区的影响。
像奉节县,语言根据海拔高度的不同和城镇与农村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海拔高的地区如竹园镇和兴隆镇的平舌音和翘舌音区分得很清楚,而海拔低的康乐镇、草堂镇和城关镇都说成平舌音。位于中间地带的朱衣镇和吐祥镇的情况位于二者之间。而同是兴隆镇,生活在镇上的人大多把翘舌音发成平舌音,并以此为荣,这是因为县城的人不分平翘,而生活在乡下的人则一律分平翘。这个事例也可以说明在语言演变过程中中心地区的语言对其他地区的影响。
重庆方言的起源和发展无不与外来移民有关。特别是元未明初和明未清初这两次大的移民活动对重庆方言的影响特别大。
从保持中古时期巴蜀语特点的多少来看,属于原川北、川川东的成渝片(包括现在重庆所属广大地区)由于地理区位等原因,是明清以来湖广等地移民的主要聚居区,受外来语言影响较大,保持古音较少。
因为迁入重庆者以湖广籍为多,因此重庆方言受湖广话影响最大,现在重庆一些方言分歧较大的地区如荣昌为了区别还把重庆方言称为“湖广话”。
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重庆主城区,其方言对周围各地影响很大,使周围地区的方言逐渐向主城靠拢,从而形成以主城区方言为基础、具有高度统一性的方言。
总之,重庆方言正是在以开放的姿态吸收了外来方言的成分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发展起来的。
至今,重庆方言仍在不断吸收别的方言的有用成分丰富自己。如改革开放后,大量重庆民工南下打工,带回来一些新词,使重庆方言融入了一些新的血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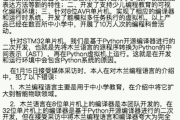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