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关公、关帝、关圣这些封号显得持之有故、顺理成章,民间社会之所以能够接受关公封神,关羽封神并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既是一部追寻关羽封神之路的著作:作者不仅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讲述了关羽成神的过程,与关羽的宗教形象之间的差别如此之大,促成关羽崇拜的并不是《三国演义》,而并非《三国演义》促成了关羽崇拜的传播,却在关羽被东吴擒获的荆州诞生了关公崇拜,就是最早出现在荆州当地用以供奉关羽的建筑物。
文·王淼
提起关羽这个名字,我们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桃园结义、单刀赴会、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这些传奇的故事,想到的是一个被供奉于地方坛庙中的神祇,是一个傩戏和各类地方戏剧中的传奇人物。
关羽这个名字,既意味着武艺高强、战功赫赫,同时也是与“忠诚”“正义”“守信用”“重承诺”等这些优秀的个人品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毫无疑问,我们对于关羽的印象很大程度上得自于《三国演义》,是《三国演义》让关羽的形象深入人心,让关公、关帝、关圣这些封号显得持之有故、顺理成章。在很多人眼里,民间社会之所以能够接受关公封神,《三国演义》的影响应该至关重要。
事实当然不会如此简单,我们知道关羽是人,不是神,他是《三国志》中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但也只是如此而已。作为三国时期蜀国的重要将领,公元219年,关羽兵败麦城,被吴军俘杀,随后即走上了漫长的封神之路——从关羽,到关公;从关帝,到关圣,渐而成为影响广泛的民间神祇,接受民间大众的供奉和膜拜。
关羽封神并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在其演变的背后显然有着某种社会环境和人文需求的支撑,荷兰汉学家田海的《关羽:由凡入神的历史与想象》,既是一部追寻关羽封神之路的著作,也是一部解析关羽的故事建构,乃至追溯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源流及其演变的作品。
在这部书中,作者不仅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讲述了关羽成神的过程,同时也对这一过程本身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论证。
审视作为历史人物的关羽,与关羽的宗教形象之间的差别如此之大,后者虽然与前者大相径庭,却已经化为人们记忆的一部分,它们自身就凝成了历史。诚如田海所言,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即是去梳理这些故事的来源,当然也就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到帝制时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层面,揭示出地方社会的焦虑,精英阶层和普通人的关切,乃至居于深宫中的帝王们的忧虑,以至更进一步地理解在共同历史背景中被建构的地方认同。
通过研究关公的封神之路,田海认为,促成关羽崇拜的并不是《三国演义》,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学传统,因为早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关羽崇拜已经颇具规模,并影响了《三国演义》的创作。在关羽的封神之路上,恰恰是地方性的口头文化传统影响了《三国演义》的创作,而并非《三国演义》促成了关羽崇拜的传播。
田海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关羽的封神之路上,与文字传统相比,口头文化显然占据着更为优先的位置。
三国大将步入神坛
公元209年,关羽发起了伐魏的战争,逼得曹操几乎迁都。曹操无奈,只得暗中联络东吴,以共同对付关羽。于是,正值关羽在樊城附近与曹仁交战时,东吴将领吕蒙率军突袭关羽的后方根据地荆州,关羽腹背受敌,西走麦城,并在突围途中被东吴擒获,与其子关平一起遭到斩杀。对此,《三国志》的记载是:“权遣将逆击羽退路,斩羽及子平于临沮。”
关羽之死既是蜀国由盛变衰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三国演义》故事情节的分水岭。对于很多读者来说,因为关羽的缺席,小说后半部分的故事明显不如前半部分精彩了。然而,随着关羽的缺席,却在关羽被东吴擒获的荆州诞生了关公崇拜,已经死去的关羽化身为一个狂暴的恶魔,既令人敬畏和恐惧,但有时候也会帮助人。其直接证据,就是最早出现在荆州当地用以供奉关羽的建筑物,以及陈列于其中的碑刻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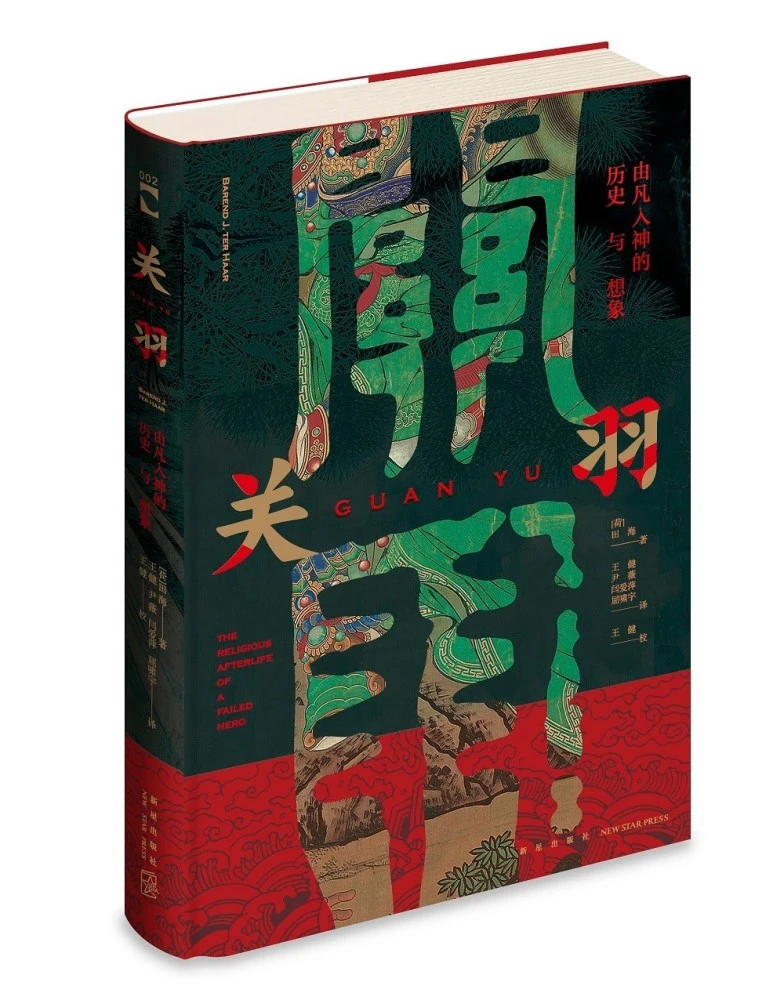
《关羽:由凡入神的历史与想象》
这在当时是一种相对新兴的崇拜类型,即人们会崇拜那些因遭受暴力横死而变成恶鬼的人,人们相信这些尚未耗尽生命力的恶鬼仍然存留在世间,对活着的人具有某种潜在的危害性。但只要这些恶鬼的崇拜者提供刚刚屠宰的动物作为祭品,祭祀者将会受到恶鬼的保护,关羽就此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具有强大能量的神祇。
与那些依赖于特定灵媒的神祇相比,人们更容易获得关羽的帮助,而对关羽的祭祀,也更容易安抚他们对于自身所处环境的恐惧与对生活艰难的不安情绪,这是此后关羽崇拜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
位于荆州当阳的玉泉寺,成为早期关羽崇拜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地点,正是在这里,关羽遭到了东吴的擒杀,进而首先被崇拜者们赋予了护法恶魔、驱邪将军的能量,而智顗与关羽相遇的传说,也成为关羽降灵最早流传的故事之一。正是以当阳玉泉寺作为起点,死去的关羽开始步入庙宇和圣坛,并被世俗大众频繁地纳入道场和各种各样的神灵附体类的仪式之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关羽崇拜被民间大众赋予了更多的内容,他已不仅仅是护法恶魔与驱邪将军,同时又是雨神、财神、科举神、医药神,乃至佛教中的伽蓝神,以及道教中的关圣帝君。
而关羽崇拜亦由地方社区延伸至更高的社会层级,关羽的崇拜者们则借助佛教或道教的流行,将他们对关羽的崇拜纳入自身的宗教信仰系统,使之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
关羽的形象,也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固定的模式:红色面庞,三绺长髯,一袭绿色长袍,胯下赤兔马,手执青龙偃月刀,时刻不离左右的还有关平和周仓……
关帝庙的诞生和普及
公元十三世纪早期,据一位为蒙古人作战的山西籍将军回忆,在他从军的早年时光,他常常梦见一位端坐在马鞍上的长髯将军。这位长髯将军总会在战场上保护他,使他在关键时刻免遭伤害,后来他在一棵蛀空的桑树下发现了关公的画像,此后每逢战役,他必拜关公,而每一次战役的胜利,他都似乎感觉到了神灵的护佑。
在关羽封神的历程中,如果说荆州当阳的玉泉寺是第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地点,那么,山西解州的关帝庙则是继当阳玉泉寺之后的第二个具有标志性的地点。
解州,既是关羽的家乡,同时也是中国北部内陆重要的产盐地,因为盐业的开发,这一地区成为北方商业的网络中心,可以轻松地传播故事。
北方的关羽崇拜即与盐的区域性贸易密切相关,在盐池的驱邪仪式中,关羽作为一名阴将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当地人看来,关羽的力量足以制服其他的邪恶生物,是没有任何疑义的盐池的佑护神。而借助那些善于讲述并传播神祇灵异故事的群体,解州的关羽崇拜通过当地的商贩、官员、武人以及宗教专家们的口耳相传,沿着商路被大范围地带到了各个地方,并在不同的区域间广泛地传播开来。
从时间上看,唐代乃是关羽崇拜走向普及的一个节点,关羽被一位佛教高僧所点化,成为伽蓝神,从此不仅是一位世俗的神祇,同时也被更多的佛教徒所接受。
到了宋元时期,关羽又被道教的张天师招募为驱魔将军,成为南方道教驱邪赶鬼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随后,关羽被宋孝宗加封为专司雨旸的英济王:“凡有祷于水旱雨旸之际,若或见于焄篙凄怆之间,英烈言言,可畏可仰。”进而成为民间兴云布雨、拯救干旱的雨神。
从明代开始,关羽被纳入了皇家的信仰框架之内,获得了朝廷的册封,并在士人群体的推动下,重构了一个更具有人文色彩的新形象。但民间社会依然还是各取所需,人们或者将关羽视作雨神,或者将关羽视作财神,而关羽的故事,则被整合为一套为民间社会所一致认同的行为准则。
毫无疑问,关羽崇拜的传播不仅表明各个区域间交流频率的增加,而且是地方神体系拟人化趋势的一个例证。尽管国家力量的介入是希望利用关羽崇拜的仪式,来显示国家在地方社会中的权威,但这并不意味着地方社会会一直盲从于官方的范式。如果说每个社区和团体都有一套在日常交往中的约定俗成、一以贯之的价值规范,那么,在传统社会中,包括关羽崇拜在内的宗教活动,正是这些价值规范的重要源头。
在口耳相传中形成的“关羽崇拜”
回溯关羽的封神之路,从早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恶鬼,到骁勇善战的护法恶魔、驱邪将军;从后来的雨神、财神,乃至医药之神、文士之神,一直到道德的典范和全能的救世主的形象……在关羽崇拜的不同时期,关羽每种形象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也无不与民间社会口耳相传的奇闻逸事密切相关。
虽然每个时代和每个阶层所讲述的关羽故事的内容有所不同,但关羽之所以世世代代受人祭祀,关羽故事的核心,则是从中体现出的对地方百姓的关心和对底层民众的帮助。
当然,作为受人供奉的神祇,关羽并不是没有条件地帮助世人,要获得关羽的帮助,人们自身也必须具备道德良善的品质。换句话说,为了获得关羽的关心和帮助,人们首先需要做好人,做好事,反过来说,人们若有失德的行为,关羽也会施以一定的惩罚。
总之,关羽既有保护人们的责任,人们也要承担一定的义务,这其实更像是一种相互成就的关系,关羽为社会道德的提升做出了贡献,关羽崇拜也理应得到地方社会的认同。正因为关羽有着惩恶扬善的终极权威,他最终成为一个在社会上捍卫这些道德原则的重要角色。
正像田海所阐述的那样,关羽的封神之路,其实是与那些有关他的灵验故事的口耳相传分不开的,这既受益于频繁的人际互动,以及由此形成的口头文化的力量,亦真实地反映出几个世纪以来关羽崇拜具有典型意义的变迁图景。
有关关羽崇拜的故事不仅受到了仪式活动、地方戏曲以及各种视觉和物化形式的支持,口头文化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得以了解不同时期的社会背景,了解人们的焦虑和期望,毋宁说正是这些故事,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理解不同时代地方社会的窗口。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