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楼又东风
福建 王清铭
我很多年的生活都与木楼板有关,但很少去注意这些承受我重量的楼板。我的目光更多投向低矮、黝黑的屋檐,感觉天空的重量压进心头。这就如我们更多关注天空,却很少注目大地。
只在失眠的夜里,比如现在,彷徨的我开始让无神的目光掷向斑驳的地板,然后被折了回来。
天空是虚的,而楼板是实在的,如生活。
四岁时,勤劳的父母建造了一座楼房,我的生活与楼板关联。但小时留下的印象极少,在乡村生活,失眠的大概只有蟋蟀和看门的狗,萤火虫也是,要提着灯笼行走。我们没有,夜幕一降,不通电的乡村就笼罩在一片睡意之中。大人太辛苦入睡早,我们这些孩子早进入梦乡,直到第二天早起的鸡将我们叫醒。
有时也在半夜醒转,听到隔壁的楼板在夜里响着,朦胧中知道父母被什么难事缠住了。那些事一般都很具体,比如播什么种,养什么猪。那是大人柴米油盐的事,我们可以不管。
渐渐长大了,楼板仍然是生活中的小配角。有时夜里也失眠,也不外乎酱醋茶,很实在的,所以失眠的时间也短。至于人生中比较重大的事情,升学、就业等,年轻的我也很少为之失眠过,脚下的楼板也很少在这些事情中用沉闷的嗓音表达过意见。
工作后分配在一所农村中学,住的也是木阁楼。教学之余写写诗歌,很清闲,但失眠的日子多了,楼板经常在半夜响起。楼下住的是一户老教师家庭,怕影响他们休息,我尽量脚步声。楼板发出的声音是压抑的,我的生活也是压抑的,一种莫名其妙的压抑感。在《曾经的承檐居》一文中,我这样记述过那时的楼板:我起床点烟,脚轻踩在楼板,楼板似乎也听出我脚步的沉重,很沉重地叫出痛苦的呻吟。
我连续用了“沉重”一词,但那时的我也不知道楼板承载什么重量。在承檐居中读过米兰·昆德拉的《生命难以承受之轻》,那时我就想那重量大概只能用这个“轻”字描述。生活真是充满悖论,我充满激情的日子也充满了青春的躁动。这也足见诗歌一无是处,除了增加失眠的长度。昆德拉还说过一句话: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现在轮到我写作这篇文章发笑了,当然是有点苦涩的笑。
楼板隔音条件差,楼下日常生活的声响毫无遮掩藏地侵占我的生活空间。家庭生活难免有口角,我的内心也在不断打架,弄得无辜的楼板也深夜难眠。
那时我爱听歌和唱歌,喜欢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我也是一只,只是被囚禁在木板建构的房屋中。最喜欢唱的是两句: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哪一个更重要?有时用我破锣嗓子狼嗥几声,困兽犹斗,但我不清楚应与什么鏖战。
李白说: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天地何尝不是一间我们寄居的大房子呢?我们都是过客,我们用什么证明自己的存在呢?
那时的我经常这样矫情地想。
笼中鸟的啼声清丽婉转,我的声音只能用聒噪来形容,再加上脚步在楼板上的伴奏,我也成了楼下那家庭噪音的制造者。但他们现在都不记得了,有谁会记得一个年轻人的躁动呢?除了彻夜失眠的楼板。
漏洞百出的楼板是难以隔绝音响的,但正在的隔阂还是人与人之间,当我在楼上悲天悯人地为楼下的教师家庭思考时,完全没有发觉在他们的心中,我是一位深居简出的“怪人”。
当我在电脑上再次敲下两个字:楼板。一种震颤的声音直冲击耳鼓,不是共鸣,而是从踟躇的脚底,通过僵硬的四肢,在沉入心底的一种颤动。楼板。楼板。楼板。盘踞了我的生活,成为主角。
我以为屋檐或天花板跟目光的联系较为密切,而楼板,与脚步和心跳一道律动。没有规则的,也没有旋律。楼板总是将脚步声吸收、传导、扩大,然后将声响送向空中,靠近耳朵的位置,直到现在,那声音还没有落下来。
不知道那时的楼板感受怎样,一切东西都有生命,只是我们没有感觉到罢了。两年后承檐居拆了,什么也没有留下。除了记忆。
我搬到了新建的楼房,钢筋水泥的,五层。社会在进步,我却在这里一住好几年,直到楼板同我的青春一样斑驳了。搬走那天,楼板上扔满杂物,布满洗不掉的痰迹,以及不断增加的灰尘。后来的人会将楼板冲洗干净,但有很多东西是冲不走的。
很自然想到李后主的“小楼昨夜又东风”,他的不堪回首,那座楼的楼板是知道的。那夜明亮的月肯定也有重量,照无眠,在楼板上留下声响。
失眠的脚步将楼板的心跳踩出。我的脑中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混乱的话,很多时候思绪是无法说清的,就如现在,我突然想起了以前的生活,内心有一种莫名的惆怅。
现在我的生活渐渐地“正常”了,那个颇有微词的“怪人”绰号也被别人和岁月淡忘。但有时深夜失眠,脚踩在冷漠的水泥楼板上,在恍然中失落的感觉随夜色越来越浓黑。
门是妥协的墙,那么习惯沉默的楼板呢?
351200 福建仙游私立一中 电话:135159307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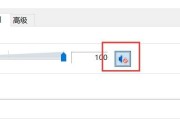




评论列表